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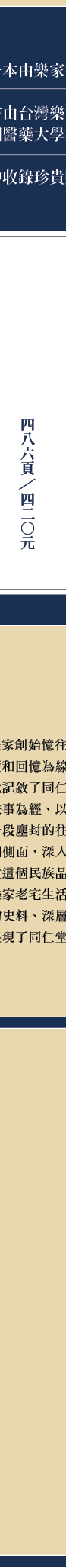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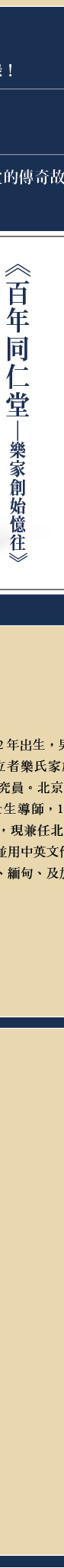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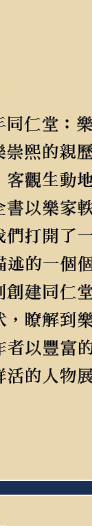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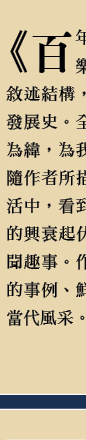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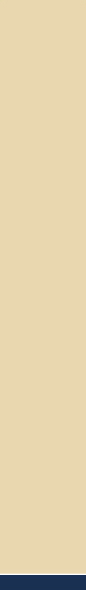
 |
|
|||||||||||||||
 |
 |
 |
 |
|
|||||||||||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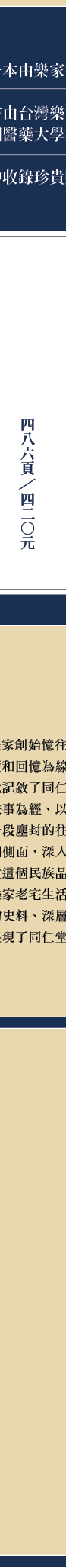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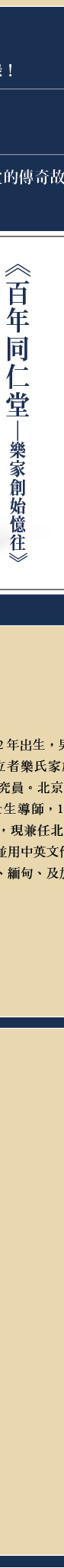 |
|
|||||||||||||
 |
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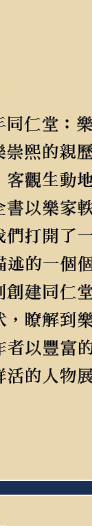 |
 |
|
|
||||||||||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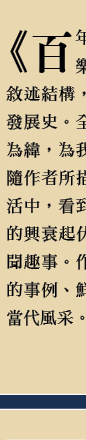 |
 |
|
||||||||||||||
 |
|
 |
 |
|
||||||||||||
|
|
|
|
||||||||||||||
|
|
 |
 |
|
||||||||||||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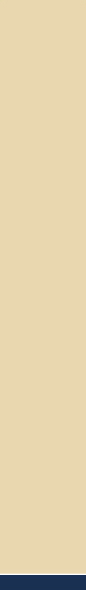 |
|
|||||||||||||||
|
|
||||||||||||||||
|
|
|
||||||||||||||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|
序一 崇熙二弟所寫的這本書,就是寫了一些咱們樂家同仁堂的點點滴滴,寫的來龍去脈沒有錯誤,就是同仁堂的一些故事。我們十五先生住在新開路六號,大四合院稱為東院,十七先生與你和崇祺、士元則住新開路十九號西院北樓。兒時遊戲的鴿子籠,還能歷歷在目,旁邊就是同仁堂製藥房。民國三十八(一九四九)我來台灣奔往台灣同仁堂五嫂樂曾璧如處任帳房,一幌半個世紀多了。空嘆人生忽爾半老,不勝唏噓之嘆。 三哥崇輝序於大乘精舍常不退齋 老宅的周邊鄰居們 老宅北口對面在打磨廠中段,有一家理髮店,父子三人經營著。筆者在初中以前,經常在此理髮。據他們介紹,樂家嬰兒的胎髮都是他家老掌櫃給理的。筆者上初一時,與老爺子嘔氣,躺在鴿子院中生氣。想到三國時曹操馬踏青苗、割髮代首的故事,馬上到那家理髮店中推去快要留成的分髮。本來師傅按我頭上的旋,順勢應該右分;二次留頭時,筆者認為初次留頭不順,請求他們為我左分。幾十年間常有理髮師傅抱怨說:「當初是什麼人沒按規矩給您留的頭髮啊,他們怎麼不按規矩來呀!」筆者笑而不答。夏天時,小理髮館沒有電扇,但他們有土法風扇,即在房頂懸二長約兩尺的布帳,拉之有風。據稱二、三十年前商家都用此土風扇,小徒弟常司此職。結帳時他們常說:「您甭給了,我候您的了!」有一次一個外鄉人真要不給錢就離去,他們忙說:「這只是老北京的一句客氣話!」 二房人所指的東院是指十五伯父的家,該宅前門在新開路東邊,在老宅的斜對面。他們的後門在北官園,東院有百八十間房,是又一個大宅院。大房人所指的東院是六伯父的家,在新開路中段路東。筆者六、七歲時的一天,佑申大嫂告訴筆者,東院六伯父家有個派對,叫我們前去吃洋點心。他家有西洋式的平房,屋外有大花園,綠地草坪,花木錯落,在東南一角落處還有轉椅,筆者很喜歡那裡,玩興熱烈。那天下午,哥媽誤帶我們來到了十五伯父家的東院,可去那後發現並無聚會,和崇輝哥、崇光弟、信、億諸姪玩了一會兒後回家。次日見到佑申之女美琪,她說:「昨天你們怎麼沒去啊?那麼多點心,吃都吃不完。」原來是六伯父家有派對,我們誤會了,大房人和二房人所指的東院並不是一個地方。六伯父家的客廳與餐廳之間有一活動木板牆,可隨意開關。六老爺常作投壺之戲,壺是一高約一尺半的瓶樣金屬物,肚稍大口較小,矩圓形的口外有兩耳,耳孔徑約一寸半,以長約二尺半的細桿(又名?)投之,投之入壺口者為勝,投入耳孔中者為大勝。筆者在人藝演的話劇《虎符》中見如姬夫人有投壺之戲,說明戰國時即有此遊戲了,今日卻鮮見矣。 出新開路南口,就是興隆街。新開路南口往東一點,路北就是四伯父家的一片豪宅,筆者僅進去過一次。一年三十晚上,去給六伯父等長輩辭歲。家人近親十幾個人,從六伯父處到四伯父家辭歲。過了多重院子,四伯父與七嫂根本不見,只在大勝家坐了一會兒。只知大勝之子有哮喘病,他叔叔大鵬讓他趕快坐下。新開路南口有個過街樓,據風水先生說此樓關係到樂氏家族的興衰,更關係到同仁堂業務的好壞。所以從二十世紀三○、四○年代,日本侵華時期和國民黨執政時期,幾次要拆去新開路南口的過街樓,都經樂家人花錢買通有關人員撤銷此議。直到解放後二十世紀五○年代初期,該過街樓終於拆掉了。 新開路北口經常停著幾輛人力車,在日本人侵華後期逮捕表兄共產黨員楊德修時,有幾個不三不四的特工人員也在這裡不時出現。新開路有兩家賣花生瓜子的小攤販,也是筆者經常光顧之所。在新開路中部路西黃安會館中的一家,攤主叫王三。白天在外擺攤,晚上踩一石從他家後窗也可以買零食,五分錢一小包花生米或鐵蠶豆。北口一個大攤,攤主孫二,原為人力車夫,五十多歲時改擺小攤,貨較齊全。賒帳時他讓筆者自記數目,一個下雨天,相當涼爽,筆者還是買了幾瓶汽水。冬日孫二耳朵生了凍瘡,他添了烤白薯,寒風凜冽,增個火爐,不過聊勝於無吧!他和王三常於清晨到曉市一起躉貨,他們倆相處融洽。 新開路中段路西有一黃安會館。清時為湖北進京會試人員所設,筆者兒時,這裡已成為大雜院,住戶有偵緝隊員、小攤販。筆者一位初中同學亦住於此,筆者邀他家中小坐,他說咱們還是街上聊吧。一天與黃安會館二青年交談,問到日前一婦人為何在街頭痛哭,俟一人離去,另一人告訴我,該涕哭者即離去人之嫂,該女士哭她去世的父親。按北京人的規矩,兒婦不當在婆家嚎喪。 |